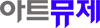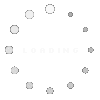| 在自主美学的交点,梦想世界的“仙界”-Kim Yujeong | |
在自主美学的交点,梦想世界的“仙界” 美术评论家 Kim Yujeong 艺术家在一生中会有多大的变化。当然根据各人偏差,其大小轻重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物性具有变化之属性,且变化正是世界的“法轮”,所以今天的我似乎已不再是昨天的我。时间在空间里被确定。因为空间的变化可令人感知到时间。因此所有事情有始有终,在开始与结尾之间的过程则从根本上使所有行为具有意义。因此开始永远是新鲜的,而结局最终是厚重的。 无疑艺术是变化的。其原因在于周围的条件与世界的潮流不容许艺术家的艺术行为保持静止状态。 所以艺术家需要在停止与运动之间自我调节本身的艺术行为,而且根据调节行为所向何处,其变化水平也会有差异。对艺术家来说,也可能存在无意识变化的时间,但也有可能下意识地估计与调节自身变化的程度。 艺术内容的问题经常遇上美学的问题。因为艺术与自身一生的问题直接相关。这种美学的问题就是所有艺术不断争取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因为艺术价值是与艺术的目的相结合的,所以追求艺术价值的问题只有当面对享受艺术的大众时,才获得意义。没有大众的艺术并不存在。大众有时会误导艺术,但艺术一直走在大众的前面,引领着他们。引领大众的艺术一直需要创新的源泉,使停在水中的苔藓流向大海。所以就有一种智慧的论点,即饮用流水不会中毒。没错。艺术就是流水。大众饮用之后也不会中毒的新鲜之水。因为有变化,所以不会腐蚀;因为保持流动,所以不会沉淀,这就是大众向往的、有价值的艺术。 崔炯瀼最近的作品尽显出变化之妙处。 他的创作上的大变化就是摆脱传统水墨的形式,引进 西洋画的技巧。当然,这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内容也大大转变了。而是渐渐地、慢慢地适应着材料的差异之变化。 当然把东方与西方绘画的差异只局限在材料的问题上,是很不明智的观点。就像穿了西装也不一定是西方人一样,材料只不过是修饰个人形象的形式,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由风土形成的东方的主体性。因此,材料不过是全新展现东方形象的工具。然而,经常使用这个工具,就会发现其已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手段,来体现东方形象的具体方法论。 现今区分东西方的标准也是由时代精神、风气、社会意识、共同体的习俗而形成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因为生活态度就是形成艺术内容的标准,所以东西方的区分就是根据我们的生活而区分的,艺术也不能摆脱它的影响。 崔炯瀼的创作给人一种“仿佛在哪儿存在,却没有在任何一处”的感觉,非常有趣。 虽然没有典型的学院式干练,但就是因为不够干练,反而远离了西洋画的理论,令人感到更加特别。自由就意味着脱离各种框架,所以自由的前提就具备了逃离因制度的束缚动弹不得的状态的积极意义。 同理可得,我们传统的民俗画也成功摆脱了文人画的制度束缚,从而展现出自由奔放与破格的一面。 像崔炯瀼这样,采用西方的材料却享受东方思维的画家不多,且这种创作也不简单。 从某种角度上看,可能是有些盲目的创作;但之所以仍然会义不容辞地走向此路,则是对长久的水墨画创作引起的表现局限性的一种反射作用。崔炯瀼的作品与用他绘制的水墨画的技巧完全不同,展现出新民俗画形式里的古拙美。这种古拙美到达的路就是向着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拙是比巧更高的境界)”的方向,开辟新的美好之路。这仿佛是只有韩国人才能体现出的(料理的)美味一样, 如果有韩国式 ‘表达的中心(正鵠)’,那么一定会有相应的 ‘区别的中心(正鵠)’。 追求韩国之美并不在于像流行一时的、样式化和定型化的象征符号的排列。展现韩国之美即为,展现韩国人的心性里蕴含的空间,或者说是通过寻找它的形象与色彩,博得韩国人的情感共鸣的状态。 当今的西方画家大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近100年期间受到了美术运动的束缚。这期间与西方开辟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帝国的力量相关。 支配经济的列强们把势力范围拓展到拥有艺术的领域,以这种力量的逻辑创作了艺术。我们的前辈画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曾为此疯狂,在殖民地时期接纳了从日本再引进的西洋画,并把它适用于专业教学之中,以致其现在存在在韩国画坛里。目前为止,仍未解决的韩国美术的外部倾向,就是因这种毫无批判的容纳之风俗而引起的。很久以来,韩国美术界就有一个任务,即一定要超越这种西方的影响与限制。 而且狭义的国际主义视角也很危险。 西洋美术史正是以欧美为中心而记载的,那么,学习这些知识的我们,从何处才能找到我们的精神呢。因为艺术就是通过精神作用产生的表现创作,所以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经验也可知,这种国际主义是怎样搅乱我们的精神的。 国际主义本质上就是从欧美主义变化而来、且以世界化的名义广泛传开的;简单地想,就是在没有自主性的情况下,站在了世界化的队伍前沿。在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情况下,还能凭什么去追求世界化呢。我才是我的主题,艺术也是由我这个主题进行的;所以没有自我主题,那么就成了没有自我艺术的“观念化艺术”,即不知不觉中蹈袭他人艺术的情况。这与没有主体性、没有目的四处辗转的漂流者的身份非常相似。 崔炯瀼出生于艺乡南部地区,很早就打下了扎实的水墨基础。水墨带给人们的舒适感是源于“诗书画三绝”之卓越表现,其内容也饱含我们过去的象征,所以可以很自然地勾起韩国人的情愫。 然而,传统的墨法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下形成的,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样式。纸张与毛笔、彩色颜料与毛笔时代相符,完全是传统时代的产物。因此,就像工具的变化引起意识的变化一样,物质文明的兴起导致了意识的迅速交替,从而引起了人生价值观与精神世界本身的变化。所以在鉴赏者的意识有所变化、用户收藏品也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传统时代的样式已经不能体现当今的时代条件了。 崔炯瀼从感觉上认识到了韩国画的局限。也就是说他通过经验已经感知到了包括以所谓的墨与毛笔为中心的文人画的韩国画或者东洋画为什么让人们感到过于清高。美术的变化过程与时代的变化过程紧密相连,一旦无视这一点,就会失去创新与独创性。 从主题方面来看,崔炯瀼也选择了看似为现实世界、却超越现实空间的另外世界。换句话说, 也可以用“乐土”,“乌托邦”,“净土”,“理想世界”等相似的词汇描述,但他用了“仙界”一词。 仙界是指人们渴望的,超越人类世界的世界。那个世界超越了现实的状况,且意味着超越残酷的“贪嗔痴”的理想世界。 月光皎洁的山坡与大海仿佛令人联想到了苏东坡的《赤壁赋》。体现耽罗的大海与深山里的江和绝壁,也就意味着作者已经在心中描绘了理想的精神世界。之所以空间是耽罗、而氛围却表现为仙境的江,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耽罗的仙界与梦想如画般世界的韩国人的思想之情感达到一致。在韩国人内心里的、无声地体现这种心态的绘画般的世界,根本上不是指超越空间的另外一个空间;而是在空间里建设另外的空间,即意味着隐藏的人类欲望的空间。也就是指精神所构建的空间,所以该领域是无法摆脱精神范畴的。 崔炯瀼对仙界的想法与《(莊子》的“逍遙游”里出现的词句相近。“逍遥游”就是脱离世俗,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逍遙游”里有“无何有之乡下”一句,是指自然原本的理想世界。有人称拥有一棵大树,却担心无法使用此树,于是庄子曰“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由此出现了上述之句。比喻为在想象的世界里种下此树,就无需担心谁会砍走此树,也无需使用此树,所以痛苦也就消失了。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所有都属于实用的世界,而且实用主义的世界就是充满担忧与烦心、伤痛与烦恼的世界。崔炯瀼的《耽罗的仙界》系列就是绘制由精神与想象构建的韩国人的心境之实景。 历史上人们一直向往乌托邦。崔炯瀼的仙界具有两种含义,即在耽罗里看到了这一点或正在努力寻求等。反过来看,能看到仙境就意味着看到了世俗的贪、嗔、痴。梦想到达仙境,虽然只是梦境,但如果它符合韩国人的“情恨”和“感意”,也就等同于看到了仙境。 因此现在应该把崔炯瀼看作以韩国画的传统为基础、试图寻求全新韩国的古拙美的作家。 正如墨西哥、巴厘岛、印第安、大养洲地区的绘画所呈现的一样,他们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在由古拙美展现的强烈民族形象与色彩之中。与以西方的干练美为主导的过去时代不同,未来时代的内容将充满民族的形象与色彩。崔炯瀼以古拙美远离西方,更加接近韩国之美;站在自主的美学交点上,面向世界人、憧憬全新的仙境。 |
|
ARTIST Criticism